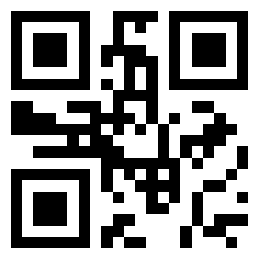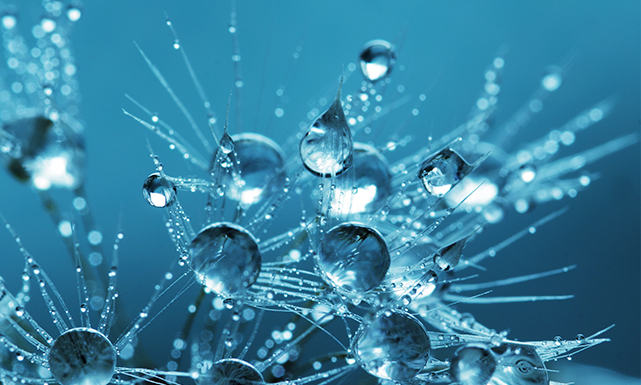我國兒童罕見病治療存在諸多困難
發布日期:2022-02-17 閱讀次數:12571 來源:中國食品藥品網
摘要:
中國食品藥品網訊 近段時間以來,各種罕見病事件屢登熱搜,成為公眾關注的熱點話題。從高中學歷父親自制“藥物”救子;到為救患有“嬰兒癲癇伴游走性局灶性發作”的孩子,幫助海外代購收寄管制藥物氯巴占被判定為販毒的母親;再到罕見癲癇疾病患兒家長求藥“氯巴占”事件……各種罕見病的輿情事件,讓罕見病,特別是兒童罕見病再次進入公眾視野。
罕見病又稱“孤兒病”,它是一類疾病的總稱,根據中國罕見病/孤兒藥定義第三次多學科專家研討會上發布的《中國罕見病定義研究報告2021》給出的定義,罕見病是指新生兒發病率小于萬分之一、患病率小于萬分之一、患病人數小于14萬的疾病,符合其中一項的疾病,即可為罕見病。罕見病雖然發病率極低,但病種多,總的患者數量并不少。目前,全球罕見病病人已超過3億,中國罕見病患者人數大約在1680萬,其中有70%的罕見病都是在兒童時期發病,這讓兒童罕見病成為各界共同關注的熱點話題。
40%罕見病患者曾被誤診 提升診療能力勢在必行
罕見病因為發病比較罕見,在臨床上往往存在診療困難。“40%左右的罕見病患者都曾被誤診過至少一次,從癥狀剛剛顯現到最后確診,可能需要經歷5—10位醫生,每年新增的罕見病患者超過20萬人,30%的罕見病患者生命不會超過5歲。”天津市兒童醫院院長劉薇在日前召開的2021年中國罕見病大會上透露了這樣一組“觸目驚心”的數據。
《2020中國罕見病綜合社會調研》中一份針對38634名醫務工作者的調查也印證了這一現狀,有4.6%的醫務工作者從未聽說過罕見病,有60.9%的醫務工作者僅聽說過罕見病對其并不了解,同時,87.6%的醫務工作者認為自己并不了解國家關于罕見病的政策。
“罕見病的醫療資源是嚴重不足的,罕見病的診斷還主要集中在北上廣這些大的國家中心、區域中心。”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兒童醫院院長倪鑫在2021年中國罕見病大會上也指出了目前兒童罕見病診療資源的現狀。
為了提升罕見病的診療能力,2018年5月,國家衛生健康委、科技部、工信部等五部門聯合印發了《第一批罕見病目錄》,121種疾病被列入罕見病目錄,首次明確了罕見病的病種,讓罕見病診療有據可依。2019年2月,國家衛生健康委印發了《關于建立全國罕見病診療協作網的通知》,宣布建立了全國罕見病診療協作網,以加強中國的罕見病管理,提高罕見病的診療水平。2019年10月開展了罕見病病例診療信息登記。2020年2月,全國罕見病診療協作網辦公室正式成立。一系列政策的實施讓我國的罕見病診療規范度不斷提升,“在美國一個病人確診平均要4.6年,澳大利亞要4.7年,而自從國家開始重視以來,我們的平均診斷周期已經縮短到3.95年。”倪鑫說。
但與普通疾病相比罕見病的確診周期依舊很長,“解決這一難題,一方面要對醫務工作者進行有效的培訓,加強醫務工作者對于罕見病以及相關領域知識的了解。”倪鑫說,“另一方面要提升醫務人員對罕見病的診斷能力,整合各方面資源,進行多學科診治,讓醫生圍著病人轉,才能盡量減少病人的就診時間和周期。”
劉薇表示,期待有一天,基層機構可以認知發現罕見病,并能夠隨訪;一、二級醫療機構可以完成兒童罕見病的初級篩查工作并做到疑似轉診;三級醫療機構負責診斷、治療和網絡的傳報,而頂層設計是由國家中心來負責,疑難處置和中心共享,罕見病患者的衣食住行、生老病死,全生命周期得到照護。
不到10%的罕見病有藥可治 讓患者有藥可用成為共同期待
診斷困難只是罕見病患者面臨的第一個難題,即使能夠確診,大部分患者依然面臨無藥可用的困境。
事實上,罕見病藥物短缺是全世界面臨的共同難題。全球大概只有不到10%的罕見病有藥可治,罕見病用藥面臨著患者少、研發周期長、臨床數據匱乏、臨床入組面臨很大挑戰、單個市場規模小等諸多困難,這些困難疊加,讓許多藥企缺乏研發或引進藥品的動力。
為了解決這一問題,美國頒布了《孤兒藥法案》并先后幾次進行修訂,通過將所有孤兒藥的壟斷期都設置為7年、給符合條件的藥物獎勵優先評審券等措施,讓藥企有利可圖,提升藥企引進或研發的動力。
近年來,我國為了解決這一難題也出臺了一系列鼓勵罕見病藥物研發、加速罕見病藥物引進的政策。
國家藥監局和國家衛健委聯合發布《關于優化藥品注冊審評審批有關事宜的公告》和《關于臨床急需境外新藥審評審批相關事宜的公告》,明確對于境外已上市的罕見病藥品,進口藥品注冊申請人經研究認為不存在人種差異的,可以提交境外臨床試驗數據直接申報藥品上市注冊申請;對罕見病藥品等臨床急需境外新藥建立專門通道進行審評審批,要求藥審中心對列入專門通道的罕見病治療藥品在3個月內審結。此外,國家藥監局藥品審評中心還陸續發布了一系列指導原則,鼓勵罕見病藥物研發。
為了加速罕見病藥物的引進,國家藥監局先后發布了兩批《臨床急需境外新藥名單》,其中包括37個罕見病治療藥物,得益于這一政策,用于治療罕見病亨廷頓舞蹈癥的氘代丁苯那嗪片,從上市申請到獲批上市僅用了不到6個月的時間,彰顯了我國政府加速引進臨床急需的罕見病救命藥的決心和執行力。
一系列政策的實施讓罕見病患者們看到了“有藥可用”的希望,但離真正實現“有藥可用”還有一定差距。“僅《第一批罕見病目錄》所涉及的121種罕見病中,仍然有47種還無藥可治。”倪鑫說。
“我國兒童罕見病藥物沒有滿足臨床需求的現象還是非常顯著的,罕見病兒童用藥還面臨著品種劑型匱乏,劑型過少等問題。”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附屬同濟醫院兒科學系主任羅小平表示,“罕見病研發是一個漫長的過程,目前通過自主研發罕見病藥品的方式,只能是遠水還救不了近火。我國先后提出了博鰲模式和大灣區模式,可以實現罕見病藥物的直接引進,讓患者盡快用上國外已經上市的罕見病用藥,解決一部分患者的藥物可及性問題。”
不過讓罕見病有藥可用仍是全世界面臨的共同挑戰。“兒童罕見病藥物研發依舊任重道遠,我們需要各方的協助,共同的努力,來提高我們兒童罕見病藥物的可及性。”羅小平說。
高昂藥費讓患者望藥興嘆 多渠道發力提升用藥可及性
“救救罕見病杜氏肌營養不良(DMD)孩子吧,他們的藥已經到海南博鰲樂城先行區了,但是價格太貴了,我們只能眼睜睜看著。”一位DMD患者思思(化名)的母親說。
不僅僅是DMD患者負擔不起藥費,大部分罕見病藥物價格都極其昂貴,高昂的醫藥費讓很多罕見病患者家庭無力承擔,只能望藥興嘆。
據《2019中國罕見病患者綜合社會調查》公布的數據顯示,對于有未成年患者的家庭來說,愿意支出家庭收入的67.4%進行干預,罕見病患者平均每年購買孤兒藥花費超過12萬美元(注:約合80萬人民幣),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,2021年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僅為35128元,相差數十倍。讓罕見病患者有藥可用,用得起藥,用的好藥成為患者與醫生的共同期待。
今年1月1日,隨著新版國家醫保目錄正式實施,渤健的諾西那生鈉注射液由70萬一針的天價降到3萬一針左右進入醫保目錄。這一降幅給脊髓性肌萎縮癥(SMA)在內的多種罕見病患者帶來希望。
諾西那生鈉注射液只是其中的一個代表,自2018年成立以來,國家醫保局每年一次動態調整醫保藥品目錄,僅2020年和2021年就分別新增7種罕見病治療藥物納入國家醫保目錄,截至目前,納入國家醫保目錄的罕見病藥品已有40余種,罕見病藥物的可及性有了顯著提升,但對于部分價格特別昂貴的特殊罕見病用藥,由于遠超基金和患者承受能力等原因,依舊無法被納入基本醫保支付范圍,目前仍有包括依洛硫酸酯酶α在內的年治療費用超百萬的高值罕見病藥物缺乏支付保障。
為了解決這一問題,早在2020年國家醫療保障局就在對人大代表的回復中表示,將進一步健全多層次醫保體系,大力推動發展商業健康保險,充分發揮商業保險風險管理和保障功能的作用,多層次提高參保患者醫療保障水平。無獨有偶,在2021年11月,國務院辦公廳印發《關于健全重特大疾病醫療保險和救助制度的意見》明確提出,探索建立罕見病用藥保障機制,整合醫療保障、社會救助、慈善幫扶等資源,實施綜合保障等,多種方式保障罕見病患者用得起藥。
北京大學醫藥管理國際研究中心主任史錄文表示,我國已經對多層次支付開展了積極探索,但他坦言國家醫保只能保基本,由于醫保資金承載能力有限,對高值藥品較難承擔。而補充醫療、專項資金、慈善和商業保險能籌措的資金總量又有限,這種狀態下只能在局部探索中不斷嘗試。
“我希望能夠建立一個全國統一、公開透明、獨立運行的罕見病診療及基金信息化的管理平臺。可以利用平臺,積極引導患者注冊登記,提供必要的診療信息,為罕見病患者提供經濟補助、生活輔助、信息與資源、服務等方方面面的幫助,慈善機構也可以通過平臺去幫助患者,甚至醫療工作者、研究者都可以通過平臺去探索新的研究方向,發現新的手段,利用新的技術,更好地服務這個群體。”史錄文說,他期望通過這樣一個平臺,讓罕見病診療技術更加發達、管理更加規范、診治更加科學、惠及更多人群,讓罕見病患者的可獲得性更好,相關的藥物可及性更高,報銷水平更高,經濟負擔下降,生活質量更優。(劉新楊)
相關新聞

醫學科普,聽得懂更要講得對
新一輪科技革命推動醫學科技迅速發展,新裝備、新技術、新藥、新方案等已深度影響“促、防、診、控、治、康”各環節,這也為健康科普提供了高水平的傳播內容和傳播載體。醫學科普是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將健康領域的科技知識、科學方法、科學思想和科學精神傳播給公眾,旨在培養公眾的健康素養,幫助公眾學會自我健康管理的長期性活動。建設健康中國,醫學科普工作具有重要意義和獨特作用。
9890個小時之前


基于質量源于設計路線的生物類似藥質量研究
24938個小時之前

淺談AI技術在COVID-19診療中的應用
25106個小時之前

“OK鏡”市場迎來變數?療效及安全備受關注
25106個小時之前